历史研究的专业性与公共关怀|专访羽戈
历史学者给大众的印象,往往是久坐于书斋中,皓首穷经,少问世事。但正如历史学家孔飞力多次向学生们提及的一句话说的那样:“一个人的思想与他的经历密不可分”,每一代历史学者的写作,其实都在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对话中完成,时代的变动往往也会在历史学者的写作中留下烙印。
当今时代可以被称得上是又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一个“技术爆炸”的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层出不穷的新型技术冲击乃至重构着历史悠久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身处其中的历史学者们也经历着与前辈不同的治史环境。
这是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一方面,当代的学者拥有越来越多地相互交流的平台与机会,在与国际前沿理论进行吸纳和对话的同时,如何在历史研究中把握史料和理论的均衡也成为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非学院派的历史写作者群体成批涌现,他们为大众读者提供了更通俗有趣的历史叙事,也为理解历史提供了更多元的视角,但也因其专业性遭遇诸多的争议。
出于对以上种种问题的好奇,我们采访了一批青年历史学者中的代表人物:仇鹿鸣、唐小兵、张仲民、李硕、高林和羽戈,围绕他们的作品,探究他们与历史结缘的心路历程,倾听他们如何回应时代赋予的机遇与挑战。
本篇是对青年历史学者羽戈的专访。
采写丨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
学术体制的专业化使得学术机构里培养出了许多专家,而不是具有公共性的知识分子。对于非学院派的历史学人来说,他们能够在具有公共性的问题意识的基础上,更没有束缚地探索历史的本相。

“研读历史不是为了去做什么,而是为了不去做什么。”——羽戈
1
历史写作:
专业性与公共性的张力
对于学院派的历史研究者来说,其问题意识或许更多源自特定专业领域内的学术脉络和研究谱系。学术作品的阅读对象是同行。这也意味着,学院派的历史研究者要与同行就一些专业议题进行对话。细分专业领域内的学术训练、青年学者评职称、发论文的压力和现代学术体制的详细分工,使许多学者专注于专业领域而忽视了学术作为“天下公器”的公共性。拉塞尔·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里遗憾地指出,知识分子的学院化和学术的专业化,让知识分子“消失在校园里”。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里提出,业余性才是知识分子的根本属性。因此,对非学院派的历史研究者来说,他们兼具研究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双重角色。他们的问题意识更多源自研究者自身的兴趣和取向
(这并不一定是私人趣味)
,他们试图通过探索历史的本相,拨开历史的迷雾,并与他们所关心的某些现实问题形成有机的连接。换言之,他们秉持着知识分子的公共性,能不受学院体制的拘束,更自如地探索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诚然,学院派的历史学家所取得的专业成就毋庸置疑,他们的专业性使得历史研究能够更加深入。许多非学院派的历史研究也许会因为缺乏专业的学术训练,在史料的选取和考证上显得有所欠缺。但非学院派的历史研究者的观察视角对学院派历史研究进行了补充。没有学术考核的压力并不意味着非学院派学人的历史研究并不专业。尤其,在当今知识公共化的时代里,史料的搜集不再只是学术象牙塔里的专利,优秀的非学院派的历史研究同样不逊于最优秀的学术论著。
羽戈便是这样的一个例子。羽戈学法律出身,多年来,在时评、影评、文化政治评论等许多领域都笔耕不辍。2007年后,羽戈转向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写作,近些年来出版了《百年孤影》、《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等历史作品。
虽然羽戈看似远离时评,研究历史,与当下知识界保持着一定的疏离,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他,从未远离过这个时代的重要议题。对中国百年大转型的关注和思考促使他打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大门。学院派的专业历史写作无疑为羽戈等非学院派的历史写作者提供了作为研究基础的范式、素材和理论。非学院派的历史研究者的历史作品也很好地为历史研究补充了必要的公共视野和社会意识。学院派历史研究者和非学院派历史研究者的互补和辩证关系,体现出历史研究中专业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张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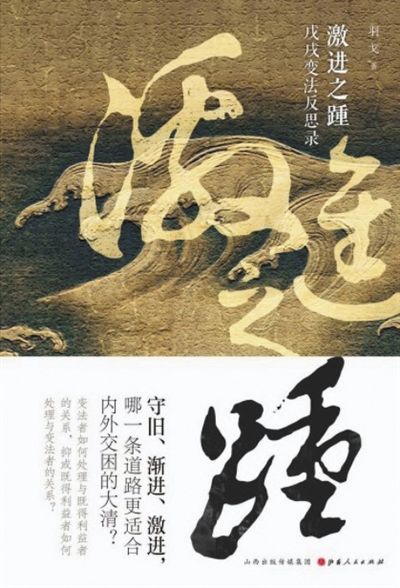
《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羽戈著,汉唐阳光|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
下一篇:没有了
Copyright © 2018 《历史研究》杂志社 版权所有